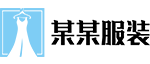拼多多的「下乡上山」五金王举曾认为,自己是改革者,和扶持低价的电商平台一起,挟低价以令江湖,把质优价廉的商品通过电商平台送到千家万户,同时,倒逼着曾经高高在上的品牌厂家降低身价走入平民大众。低价,也是他几乎唯一与品牌拼杀的优势,让他有种打土豪的快感。
但直到自己走入死胡同,他才意识到,自己不是改革者,而是“被割者”,“自己像一把镰刀,锈迹斑斑了,被扔掉了。”
王举开始反思,最近10年,我们的线上经济快速膨胀,却没有像十年前那样诞生出御泥坊、尼卡苏、韩都衣舍一样的线上品牌,甚至那些曾经崛起的线上品牌,被逐渐淹没了,为什么?假如企业的终极目标不是利润、品质、品牌,那又是什么? 电商和实体,该是怎样的关系?
从2024年12月开始,我们以“低价、品牌、未来”为关键词,拜访了数十位快消第一线个多月时间中,我们的足迹遍布数十个省市地区;同时为保证结果的真实全面性,我们还使用了线上交流、线下探厂、一对一访谈等多样研究方法,期望展开一幅真实的产业带「浮世绘」。
王举,邢台人,北京本科毕业后就去南方沿海城市一家外贸公司上班,从最开始的程序员逐步换行为运营。打包、发货、客服、运营、投流每一步都是踏实自学。后来回老家的时候发现当地的玩具产业在拼多多上面做的如火如荼,自己初中毕业的表哥每个月都能靠着自己家的小作坊每天通过拼多多销售赚几百上千块钱。
创业初期,由于资金不够,王举和他父亲在亲戚手中借了15万,还刷了7000块钱的信用卡,勉强凑钱买了自己人生一个模具,还是三手的。
刚开始王举拼多多店铺就十来条链接,其中只有一个核心扭扭车是自己工厂生产,其他的都是从表哥工厂拿货走一件代发。但是当时表哥要求,王举上架的同款产品必须比他的售价贵15元以上,不然拒绝供货。
那个时候,扭扭车在拼多多上面可以卖到130-150块钱,差一点的大概在50-80块钱,但是价格百元以下的产品质量都很差。当时拼多多的玩具类目运营的策略就是:抄爆款 降低质量 低价 出单。
在正式运营1个多月之后,王举的拼多多店铺每天能够出100单,核心爆款扭扭车的售价在79元,自己生产的成本在47-50元之间,每天都有两三千的利润。在店铺运营半年的时候,已经可以每天稳定出300-500单,老婆也从深圳辞职回到老家和王举一起做,并且一直保持了每年更新3-5款新品的节奏,同步开设了3家拼多多店铺,形成矩阵。
2020年的时候,王举的小舅子过来投奔,在工厂学了半年玩具车的生产之后表示自己也要学习开一下拼多多店铺,在老婆的劝说下,王举同意了,并且还给小舅子全开放自身店铺的数据和运营技巧。在业务稳定持续增长的时候。他和老婆并没有选择买房,而是把全部的积蓄又投入到工厂之中,购买了3套新的模具并且又增加了20个工人。
心烦意燥的王举经过一番排查之后,发现相同的搜索关键词下面新排上来的店铺竟然是自己小舅子的店铺,全部一比一抄袭王举的产品,并且价格还便宜10%。这一操作直接让王举和老婆傻眼了,怒气冲冲王举找到小舅子理论一番。
小舅子表示自己也没想到这样子,并且现在也不好处理了,因为自己的工厂和店铺里有着同学的投资,需要承担责任。就这样,王举和小舅子两个人互相比降价煎熬了3个月,最终的结局是王举的工厂倒闭,变卖资产才勉强发完工资,小舅子的工厂也草率的收场。
王举总结:“第一是当时不够成熟,没有迅速放弃一个已经开始死掉的品,在拼多多,除非你的东西别人永远做不出来,否则只要被同行盯上,这个品就算死了。第二,低价竞争,打价格战,最后大家一起玩完,谁也别想活,而且平台不会管这些山寨小厂子,平台的规则里有,发现人家比你便宜就是可以马上退款。从疫情开始,拼多多的价格战越来越激烈,我们村开厂子做玩具的几个初中同学,厂子也倒闭了。现在我们镇上就一些大厂子还能活着,小作坊都快绝迹了。”
他感叹,以前我认为自己是英雄,现在才发现,自己是平台的镰刀,收割完了,自己锈迹斑斑,被抛弃了。
中西部的作坊有过2个黄金发展周期,第一个周期在2005年到2010年,当时助推快消制造业发展的平台主要是百度,数十万计的中小企业制作产品网站利用SEO和百度竞价快速的获取客户,形成自己产、展、销的商业链路。
第二个发展周期,现在还在进行中,这一周期的主角平台就是拼多多,从2017年到2024年,这也是我们本文将要深入讲述的故事。
李华(化名)就是一位标准的“作坊主”,从2018年开始在河南焦作开了一家密胺餐具工厂。当时,主要供应给附近村里的年轻人。
“当时,村里的小青年不去打工,在家开一个拼多多店铺,一年就能挣十几二十万。一个村子,有一半以上的年轻人在做拼多多”,李华说,“当时的拼多多90%的销售都来自自然流量,客单价利润率在20-30%,每个月不需要精细化运营都能赚5、6万。”
雨后春笋一样的拼多多店铺,也培育了一批工厂,有人为了抓住这个风口创业,借钱开办工厂,专门为线上店铺供货。
从2022年开始,拼多多的流量分配机制从自然流量逐渐改变为付费流量,需要店主充值去投放直通车付费买流量,还有就是产品需要不断地低价。
附近村庄的店主李橙说,“我们没钱买流量,就卷低价呗,谁家工厂拿货价格低,我们就选那家的货。”
李华说“我最早刚开始卖的碗,一个碗卖4.8块钱。现在卖到2块多,最后无非把原先的质量一点一点往下降,做的越来越薄。”
董允所在的河北省清河县生产了全国90%的雨刮器,当地有完善的产业链,董允也有自己的工厂,常年保持30个工人的规模。
“我12年开始做网店,最初的想法是,把品质越做越好,价格越卖越高,开始我做38的雨刮器,后来我做68的,成本越投越多,价格越来越高,品质也越来越好,然后就能支撑我做品牌,开京东店,开天猫店,给大的汽车厂商供货。”董允说。
“这些就是工业垃圾,但是它卖的好啊,九块九,对于现在的老百姓来说,半包烟,就算拿来不好用,用几天扔了,他心里也不会觉得太亏,但是对我们这些想做好雨刮器的就是沉重打击,我真的好的雨刮器卖不动了。”董允一直叫骂着工业垃圾,但他为了生存,也开始调整自己的价格体系,从原来的68,降价到38、28。背后的逻辑,董允挤了挤眼睛说,“你懂的。”
当地另一位商家说,为了低价,卷到了各个环节,原先用纸箱子发货,后来用袋子发货,后来用回收料,直接去废品站收,现在清河有生产包装袋的,生意是和废品收购站绑在一起的。
董允说,“商家看似聪明了,发现最后苦的是自己,消费者也都被骗的明白了,发现这个东西不合适我就退,反正商家买单,陪着平台来玩,平台用低价收获了用户,把自己做大,商家聪明反被聪明误。”
董允说,在清河县,一度出现一门新生意,就是一些人利用拼多多套钱,“我没有钱,我去做电商,我亏钱去卖,然后我拿给工厂看,你看我一天能卖几千单,你来和我合作吧,于是商家眼红了,就放心把货给我,卖出了货,从拼多多收到货款,我不给你工厂。”
董允提醒说,“后来这些人在我们这里混不下去了,拿着这套路去浙江、广东玩了,那边的工厂要小心哦!”
张生,一位生于河北长在仙游的老家具人。他的父亲在90年代背井离乡去仙游,经过数年的拼努力,2005年成立了自己的家具加工厂,到2015年的时候工厂有员工20人左右,产品的侧重于仿古家具,每年的产值也有2000多万,主要的产品销路集中于三四线家具大卖场和贴牌、京东三个渠道。
在2018年机缘巧合接触到拼多多“中西部小产业带扶持计划”,当时拼多多希望帮助像张生这样的中小企业通过电商把产品销往全国,还特别强调会在平台初期结合“百亿补贴”提供大流量倾斜和政策支持。
2019年初,张生的家具正式上线拼多多平台。为了迎合平台的用户群体,张生将几款热销产品重新包装,推出了“简约衣柜”和“经济型书桌”,并用拼多多建议的定价策略——“击穿心理底价”——将价格压到了行业最低。
据张生说,刚开始的几个月,拼多多的流量倾斜效果明显,张生的产品多次被平台推荐到首页,单日订单量甚至突破了上百单。当时工厂24小时连轴转,招了几十个临时工也忙不过来。拼多多的小二经常打电话来鼓励张生:“张总,再扩大点产能!现在是拼多多重点扶持产业带的阶段,销量只会越来越好!”
张生动了心,添置了两条生产线,厂里的规模几乎翻了一倍。然而好景不长,从2022年开始,张生的流量开始不增反减了,张胜回忆到,当时拼多多把能获取流量的渠道全部关掉,只留付费投流直通车,小二的解释是“现在商家多了,流量分配没以前那么集中。但你可以投点广告,效果会很好。”
张生说,如果你开始去投直通车,你会发现这是个坑,举例子说,第一次你投一千,效果很好,能给你带来价值三千的流量,第二次投两千,带来四千的流量,第四次你投八千,也就只能带来八千的流量,后面你再投,流量和没投差不多。
现在的张生格外后悔,放弃了自己原本优势的“品质”仿古家具的企业策略,现在整个企业就像呆在半空中的猴子,上不来下不去。一方面是拼多多的销售“综合成本”在飞速的增长,同类产品的数量在不断地增加,产品的销售也在快速的下降,导致整体利润不断被稀释。另一方面由于产品从品质改变为快消,导致整个企业的运营、管理、原材料都是围绕快消来进行构建,如果再转回品质可能又要推倒重来。
澄海做玩具的徐天逃过了20年的外贸订单荒,但没有逃过低价漩涡。他在澄海有个50多人的玩具工厂,主要生产汽车玩具,主要渠道是出口,线下参加展销会,包括去国外线年疫情开始,出口受限,出现订单荒,我开始着手线上渠道。当时,有已经摸索出一条自己很得意的路径,通过tiktok、亚马逊推广玩具,被推广的玩具相关订单涌入到to B的国内电商平台,现在想国内外双频发展,结果发现“产品出得去,回不来了。”
原来,徐天每年都会开发新款汽车玩具,整个初期的设计开模成本不低于4万,价格策略会定在每一个产品的利润6元左右。现在徐天批发价20的产品在拼多多售价只需要15元,徐天明确表示这些产品是我开发设计的但不是自己生产销售的,作为开发者,他却做不到抄袭者的低价。
最终,徐天开发的国内版产品只卖了3000辆,库房里积压了十多万辆国内版产品,单仓储一样成本,每个月都要亏去几万。
现在的徐天的情况就是外贸稳定有钱赚,国内低价被抄袭。出去做不大,回来争不过。因为此事徐天还曾找到过拼多多的小二和相关负责人,希望解决自己产品版权被抄袭的问题,拼多多的人建议他去投诉或者法院起诉。这无疑又增加了他的维权的时间、经济成本。
徐天说,你明明知道企业要长远发展,不能走低价,不能走低价平台,但是你不走,别人走,你不走,别人用你开发的产品走,他们走我们的路,让我们无路可走,我们很矛盾。
张雷,是一名图书行业创业者,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做图书行业已经有十几年,经历了传统渠道、线下渠道、当当、京东、拼多多等多个行业发展阶段,也从一个懵懂新人变为现在风口浪尖的一线企业负责人。
张雷说他们企业开始接触拼多多的时候,拼多多的小二说了一组数据,让他从业十几年的认知被推翻,拼多多上童书类目的平均成交客单价还不到4块钱。
张雷说,我们开发的单本童书价格都在10元以上,一个系列(比如8本书)的售价在100多元。更让我们难以理解的是,同类产品在拼多多上同行商家的售价才30多元。
当他们从拼多多买来同类图书对比,发现无论从图书的材质、印刷、色彩、甚至尺寸都会很大的不同,面对这些图书,他们公司几个高管当场拍桌子喊 “这么做图书,就是慢性。”
“平均客单价不足4元,而行业平均水平在15元左右,在拼多多上面做图书大概得毛利率在10%”,张雷说,“这么低的利润,怎么养编辑,怎么养画师,养不起,怎么开发新品?”
“这么做图书,就是慢性”这句话是张雷公司高管们的共识,但有关是不是要降低品质和价格的路线之争在公司没有中断过,这还导致两个高管的离职。
在我们走访中西部和长珠三角两个区域之后,我们又选取了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的多家公司调研,他们是低价路线的回避者。
李贵的宠物公司核心产品主要是宠物主粮,公司自己研发了大概10个SKU,分为低中高三挡,客单价39元-299元不等,产品的生产加工由深度合作的后端工厂完成。
李贵的宠物主粮拼多多电商生涯从开始到放弃只有3个月。第一个月开店因为促销选取了低价策略,每天自然流量都能出几单,但是随着店铺稳定和Sku的增加,除了自然流量的减少还出现了一个严重问题,就是“仅退款”的比例越来越多,从最开始的每天1-2单到最高峰时候接近20%比例的仅退款。
李贵说到:“拼多多为了自己获取更多的流量和转化率,全站强推仅退款,你商家开店的时候如果不开通仅退款你就没有流量和订单,并且在日常运营的时候每天都会给你推仅退款开通通知。最后如果你商家想卖货,就必然屈从开通,开通了好处就是订单和流量会多一点,但是现在整个风气都被带歪了。”
据吕颖说在轻奢箱包或者轻奢行业,官方和拼多多合作是一件“减分”的商业行为,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是拼多多“假货”“低端”的标签化太严重,对轻奢的品牌会造成极其严重的损伤。吕颖说:“试想一下年轻有自己独特审美的‘富二代消费者’看到自己背的包在拼多多上面也有卖,或者和某个乡镇女生撞包,他们会迅速把你拉入黑名单。”
除了品牌方面的顾虑以外,吕颖还认为所谓“轻奢”本身的消费群体就相对较窄,或者说独特,在拼多多上面寻找价值消费者无效运营的因素会更大,与其把企业的时间、精力、金钱花在无效的人海战术之中,还不如做“减法”,聚焦寻找更精准的价值消费者,并为其提供超预期的服务和产品。拼多多的核心用户群体还处于满足最基础的生活需求,对于消费升级的消费理解、购买行为、甚至支付能力都与“轻奢”定位不契合。
在走访中,我们还遇到广东一家“硬刚过”低价平台的企业,这家企业主要生产芦荟胶等个人护理产品,公司市值超过百亿,线上销售渠道主要是京东、天猫、抖音,并未和拼多多有过任何合作,但是从2023年之后就陆续发现,拼多多竟然销售低于1.5元的芦荟胶,这对于企业的品牌、定价、市场、渠道都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当时企业积极的找到平台的多次沟通,均石沉大海。后来这家企业无奈,投入专门的人力去打假,跑到村里作坊里去暗访,报警去抓人,但是拼多多还是有那么多假冒产品正在销售。
无论是天猫、拼多多、还是快手抖音,归根结底都是电商生意。电商生意的本质就是左手海量流量右手优质供应链,中间做个展示撮合交易平台。平台不择手段解决自己赖以生存的流量问题,供应链如何解决呢?
拼多多想要满足产品端的多快好省,第一目标当然是珠三角长三角的规模产业集群。但是这一区域受外贸和电商的影响,拥有相对稳定的产品销售能力和品牌塑造意识,拼多多单纯的低价模式很难触动供应链的质变,因为单纯的低价模式既会损害他们原有的价值销售渠道,也会影响产品的质量和品牌,这一点南方的企业电商人想的很清楚。
在这个时候拼多多则做出了一个“平替”战略,直接下乡上山,广泛的发动山东、山西、河南、甘肃、青海、内蒙等内陆地区的小作坊能力,给予这些小作坊扶持,让他们根据自身的区域和产业特点进行产品的“升级和换代”,通过数以万计的乡镇小作坊,快速的完善自己的产品供应链,还能完成“低价”的平台战略目标。
这些中西部小作坊主,普遍缺乏强大的资金实力、创新设计能力、长远品牌规划能力,整体抗风险能力,所以他们会更加依赖平台,也会更听从平台的安排,这也能让电商平台更快更低成本的实现自己产品层面的战略目标。
但是小作坊主和拼多多的蜜月期还没有超过3年就已经出现了裂缝。拼多多在完成第一阶段的草莽蒙眼发展之后,也需要完成品牌、流量、产品的升级迭代,急需摆脱外界对于拼多多低价、抄袭、假货的认知,不得不继续攻克长三角珠三角以及北上广。
拼多多已经用低价“阉割”了中西部企业的创新能力,现在又要用“低价市场”逼迫南方企业顺从。近些年来,社会各界对于拼多多的诟病之声日益增多,究其原因随着新质生产力被倡导,消费者对于产品的要求也会从低价逐步的升级为品牌、享受、美观、价值,而拼多多赖以生存的低价模式并不能满足这一升级需求。
从拼多多平台角度来看,他们已经发现了这一致命的弊端,也进行了相对应的改变,比如推出百亿补贴塑造核心品牌购买认知;推出产业带补贴政策,推动新质生产力升级和发展,但是取得的成果不慎理想,甚至商家番禺总部围楼、五粮液打假拼多多等事件不断地出现,这也预示着拼多多的发展来到“矛盾期”。
首先,拼多多的低价策略造就了一大批“商家”和内部高管,以及追求KPI的考核体系文化,这一部分人和事作为既得利益者排斥甚至打压拼多多的产品升级、品质升级、品牌升级;
其次,拼多多长期给外界的“不良印象”和现行的流量订单分配机制,对于想要合作的品牌、新锐商品造成了精神和物质双重的阻碍,往往结果都是浅尝即止,这也导致产品供应链的一直无法完善升级和迭代。
从商户角度来讲,企业内循环的的第一需求是产品的快速销售,长远需求是企业发展和品牌的构建。拼多多现在只能给予商家“0利润”的产品销售,更不能给予商家品牌护城河的塑造机会。
无论从拼多多还是商户两个角度来看,拼多多的品牌升级、产品补贴、新质提升都是可望不可即的水中月。
深陷低价漩涡的中西部作坊也好,在漩涡旁边徘徊的长三角、珠三角也好,拼命挣脱漩涡的北上广市值百亿的企业也好,如王举所言,“我们最后发现都在一个棋局上。”